rules of the game 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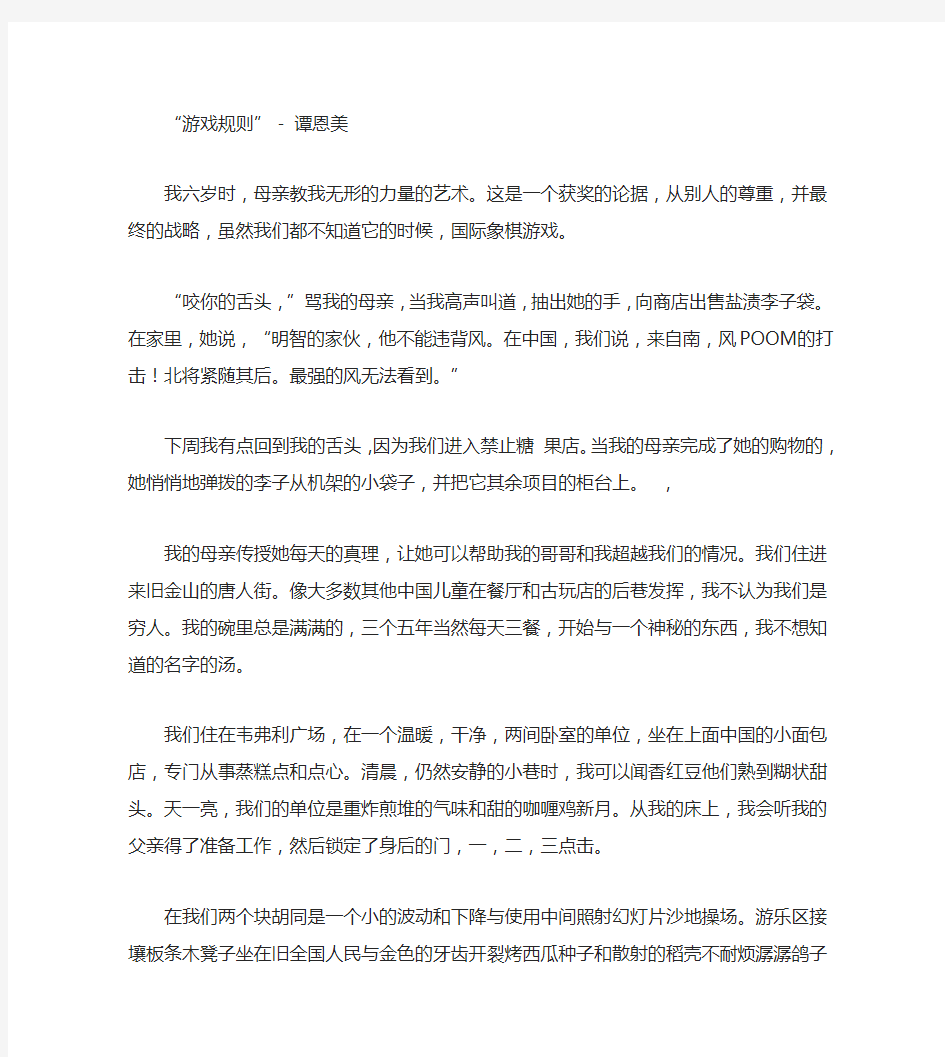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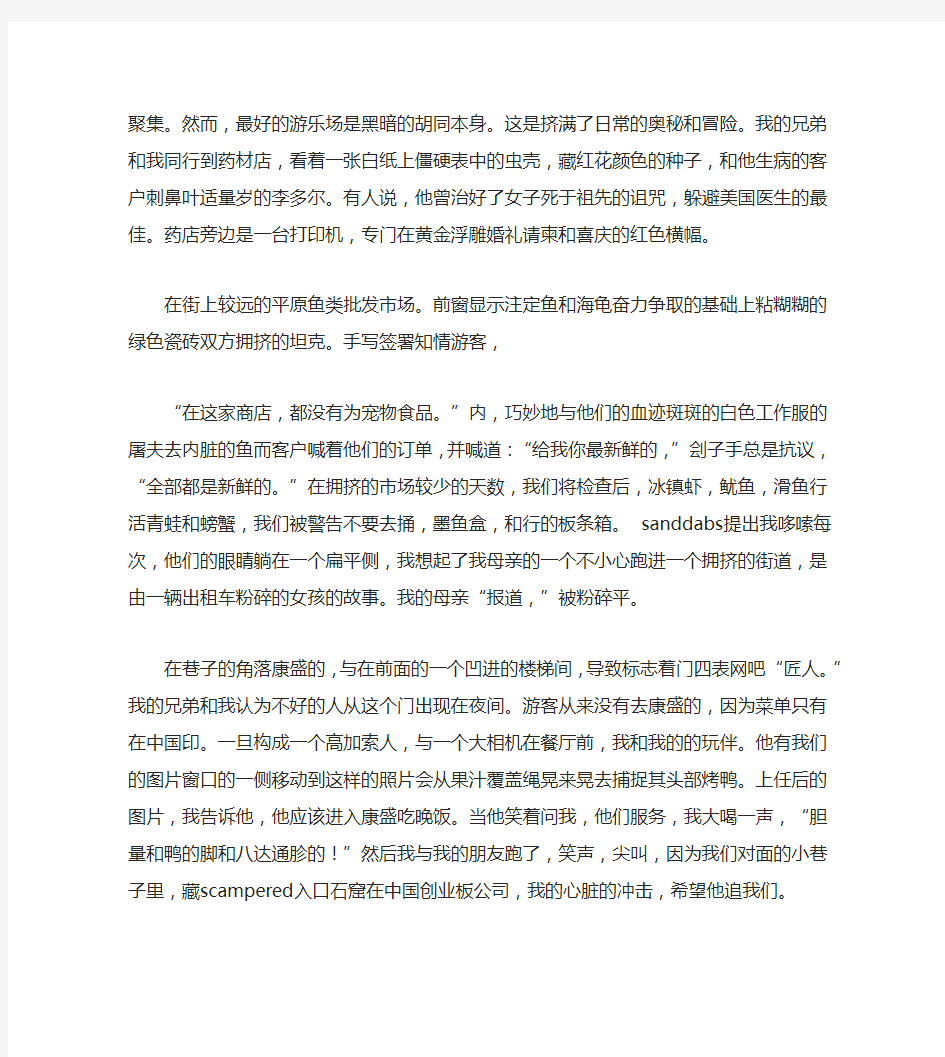
“游戏规则” - 谭恩美
我六岁时,母亲教我无形的力量的艺术。这是一个获奖的论据,从别人的尊重,并最终的战略,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时候,国际象棋游戏。
“咬你的舌头,”骂我的母亲,当我高声叫道,抽出她的手,向商店出售盐渍李子袋。在家里,她说,“明智的家伙,他不能违背风。在中国,我们说,来自南,风POOM的打击!北将紧随其后。最强的风无法看到。”
下周我有点回到我的舌头,因为我们进入禁止糖果店。当我的母亲完成了她的购物的,她悄悄地弹拨的李子从机架的小袋子,并把它其余项目的柜台上。,
我的母亲传授她每天的真理,让她可以帮助我的哥哥和我超越我们的情况。我们住进来旧金山的唐人街。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儿童在餐厅和古玩店的后巷发挥,我不认为我们是穷人。我的碗里总是满满的,三个五年当然每天三餐,开始与一个神秘的东西,我不想知道的名字的汤。
我们住在韦弗利广场,在一个温暖,干净,两间卧室的单位,坐在上面中国的小面包店,专门从事蒸糕点和点心。清晨,仍然安静的小巷时,我可以闻香红豆他们熟到糊状甜头。天一亮,
我们的单位是重炸煎堆的气味和甜的咖喱鸡新月。从我的床上,我会听我的父亲得了准备工作,然后锁定了身后的门,一,二,三点击。
在我们两个块胡同是一个小的波动和下降与使用中间照射
幻灯片沙地操场。游乐区接壤板条木凳子坐在旧全国人民与金色的牙齿开裂烤西瓜种子和散射的稻壳不耐烦潺潺鸽子聚集。然而,最好的游乐场是黑暗的胡同本身。这是挤满了日常的奥秘和冒险。我的兄弟和我同行到药材店,看着一张白纸上僵硬表中的虫壳,藏红花颜色的种子,和他生病的客户刺鼻叶适量岁的李多尔。有人说,他曾治好了女子死于祖先的诅咒,躲避美国医生的最佳。药店旁边是一台打印机,专门在黄金浮雕婚礼请柬和喜庆的红色横幅。
在街上较远的平原鱼类批发市场。前窗显示注定鱼和海龟奋力争取的基础上粘糊糊的绿色瓷砖双方拥挤的坦克。手写签署知情游客,
“在这家商店,都没有为宠物食品。”内,巧妙地与他们的血迹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的屠夫去内脏的鱼而客户喊着他们的订单,并喊道:“给我你最新鲜的,”刽子手总是抗议,“全部都是新鲜的。”在拥挤的市场较少的天数,我们将检查后,冰镇虾,鱿鱼,滑鱼行活青蛙和螃蟹,我们被警告不要去捅,墨鱼盒,和行的
板条箱。sanddabs提出我哆嗦每次,他们的眼睛躺在一个扁平侧,我想起了我母亲的一个不小心跑进一个拥挤的街道,是由一辆出租车粉碎的女孩的故事。我的母亲“报道,”被粉碎平。
在巷子的角落康盛的,与在前面的一个凹进的楼梯间,导致标志着门四表网吧“匠人。”我的兄弟和我认为不好的人从这个门出现在夜间。游客从来没有去康盛的,因为菜单只有在中国印。一旦构成一个高加索人,与一个大相机在餐厅前,我和我的的玩伴。他有我们的图片窗口的一侧移动到这样的照片会从果汁覆盖绳晃来晃去捕捉其头部烤鸭。上任后的图片,我告诉他,他应该进入康盛吃晚饭。当他笑着问我,他们服务,我大喝一声,“胆量和鸭的脚和八达通胗的!”然后我与我的朋友跑了,笑声,尖叫,因为我们对面的小巷子里,藏scampered入口石窟在中国创业板公司,我的心脏的冲击,希望他追我们。
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我们住在街上我:韦弗利广场钟,我的正式名称为美国重要的文件。但我的家人叫我妹妹,妹妹。“我是最年轻的,唯一的女儿。每个早晨
ING在上学前,我的母亲会扭曲和对我的浓密的黑发中抽出,直到她已经形成了两个紧密伤口的辫子。有一天,她挣扎着编织,通过我的不听话的头发硬齿的梳子,我有一个狡猾的思想。
我问她,“妈,什么是中国的酷刑?”我的母亲摇摇头。一个发夹,她的嘴唇之间的楔形。她湿了她的手掌和平滑我的耳朵以上的头发,然后推在这样的脚,它大幅缺口对我的头皮。
“谁能说这两个字?”她问没有一丝知道我是如何邪恶。我耸耸肩我的肩膀说,“有人在我的课的男孩说,中国人做中国的酷刑。”
“中国people.do很多事情,”她只说了一句。“中国人做生意,做医药,做画,不喜欢美国人民懒,我们做的酷刑。酷刑。”
我的哥哥文森特是一个究竟是谁得到了国际象棋。我们已经巷子年底中国第一浸信会教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传教士们一起把圣诞老人的另一个教会成员捐赠的礼品袋。的礼物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有不同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分开的麻袋。中国教区居民戴上圣诞老人服装和一个僵硬的纸胡子,用棉球粘。我想的人以为他是真实的东西,唯一的孩子们太年轻,不知道圣诞老人是不是中国人。当轮到我了,圣诞老人的人问我,我是多么老。我认为这是一个技巧问题,我是中国历法的7根据美国的公式和八个。我说我是生于1951年3月17日,。这似乎满足他。然后,他郑重地问,如果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被今年,我相信耶稣基督,并服从我的父母。我知道,唯一的答案。我点点头,回到平等的严肃性。
看着年纪较大的小孩打开他们的礼物,我已经知道,大的礼物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女孩,我的年龄了一个大着色书“圣经”字符,而一个不那么贪婪的女孩选择了一个小盒子收到一个玻璃小瓶薰衣草花露水。盒子的声音也很重要。一个10岁的男孩选择了一个盒子,jangled时,他摇摇它。这是一个世界锡全球插入钱缝。他一定以为它是助攻和镍,因为当他看到这短短的十便士,他的脸爱上了这种毫不掩饰的失望,他的母亲拍打他的头一侧,并带领他的教堂大厅,道歉,人群有这种不文明的举止为她的儿子,他不能明白这样一个优良的礼物。
正如我到麻袋里张望,我赶紧手指剩余的礼物,测试自己的体重,想象它们包含什么。我选择了一个沉重的,紧凑的一个包裹在银光闪闪的金属箔和一个红色的缎带。这是一个救生员12包,我花了党的休息安排,在我最喜欢的的顺序重新排列糖果管。我懒得温斯顿选择以及明智的。他目前横空出世,是一个复杂的塑料部件的盒,包装盒上的指示,宣布他们正确组装时,他将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战争11潜艇的微型复制品。
文森特得到了国际象棋的设置,这将有一个很体面的礼物,在教会的圣诞晚会,除了它很明显使用,我们发现后,它缺少一个黑色的棋子和一个白衣骑士。慷慨地感谢我的母亲未知的恩人,他说:“太好了,成本太高。”在这一点,细白,稀疏的
头发的老太太点点头对我们的家庭和一个呼啸耳语,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当我们回到家时,妈妈告诉文森特抛出了国际象棋的设置。“她不希望它,我们不希望它。”她说,直挺挺地一紧,得意的笑容,一边折腾她的头。我的兄弟充耳不闻。他们已经排队的棋子,从狗耳指令书阅读。圣诞周期间,我看着圣文森特和温斯顿发挥。棋盘似乎持有精心制作的秘密有待解开。棋子多岁的李神奇的草药,治愈祖先诅咒强大。和我的兄弟穿着这样的严肃的面孔,我相信的东西是在大于匠人的大门,以避免康盛股份。
“让我来!让我来!”我之间的游戏,当一个弟弟或其他会坐在一起的救济和胜利的叹息哀求,其他恼火,无法放手的结果。在第一次文森特拒绝让我打,但我作为替代按钮,填补缺件提供了我的生命拯救时,他动心了。他选择的口味:黑棋子和白骑士薄荷野樱桃。优胜者可以吃。
由于我们的母亲撒上面粉,并推出了蒸饺,这将是我们的晚餐,那天晚上,文森特解释规则,指向每一块小面团界。“您有16件,这样做一,一个国王和王后,两位主教,两个骑士,两个城堡,和八个卒子。”马前卒只能向前走一步,除了第一招,
然后,他们可以将两个,但他们只能采取这样的移动交叉男子,除了在开始时,你可以向前迈进,并采取另一种典当。““为什么?”我问,我提出我的的棋子。“为什么他们不能移动更多的步骤?” “他说,”因为他们的走卒。
“但是,他们为什么去交叉采取其他男人?为什么不存在任何妇女和儿童?”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吗?为什么你必须总是问愚蠢的问题?”问文森特。“这是一个游戏规则,我没有让他们见书在这里。”他捅在他手中的棋子的一个页面。“棋子。P - A - W - N。棋子。自己。”
我的母亲拍了拍了她手中的面粉。“让我看看书,”她平静地说。她的网页扫描快速,不读外国的英文符号,似乎没有特别刻意搜索。
“美国的这一规则,”她最后的结论。:“每个人来自外国的时间,必须知道的规则。法官说,你不知道,太糟糕了,回去,他们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你就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前进,他们说,
不知道为什么,找出自己。但他们知道所有的时间。更好的你,找出为什么自己。“她扔了满意的笑容她的后脑勺。
我发现所有的为什么。我读了规则,并期待在字典中的所有大词。我从唐人街图书馆借来的书。我研究每一个棋子,努力吸收每个所载的权力。
我学到了开放的举措和重要的是要控制中心早在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直线下降,中间是。我学到了中间的游戏,为什么两个对手之间的战术冲突的想法一样,谁扮演好一个有攻击和陷阱的最清晰的计划。我了解到为什么它是在残局中,必须有先见之明,对数学的理解了所有可能的行动,并耐心;所有的弱点和优势越来越明显的强敌,都掩盖一个累人的对手。我发现,整场比赛必须收集无形的优势,在比赛开始前,看到结局。
我还发现,为什么我不应该透露“为什么”给他人。隐瞒一点点知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应储存供日后使用。这是国际象棋的力量。这是一个游戏的秘密,其中一个必须显示,从来没有告诉。
我爱我发现六十四黑色和白色的广场内的秘密。我仔细地画了一个手工制作的棋盘和寄托它旁边的墙上我的床上,我想了几个小时盯在虚战斗。不久,我不再丢失任何游戏或救生员,但我失去了我的对手。温斯顿和Vincent决定,他们更感兴趣的漫游后,在他们Hopalong卡西迪牛仔帽学校的街道。
在一个寒冷的春天的下午,我绕道步行从学校回家时,通过在操场,在结束我们的胡同。我看到一组的老部下,两跨坐在一个折叠表打一盘棋,其他烟斗,吃花生,并观看。我跑回家,抓住文森特的国际象棋,这是在纸箱中的约束,用橡皮筋。我还精心挑选了两个珍贵的生命拯救卷。“我回来了公园,走近一个人,谁是遵守游戏。
“想玩吗?”我问他。他的脸拉大感到惊讶,他笑了,他在框看了下我的胳膊。
“小妹妹,过了很久,因为我的娃娃发挥,”他说,微笑着仁慈。我赶紧把箱子下他在板凳上,并显示我的反驳。
刘蒲,因为他让我给他打电话,原来是一个更好的球员比我的兄弟。我失去了很多游戏和许多救生员。但几个星期,每个糖果减少轧辊,我增加了新的秘密。刘宝给我的名字。从东,西岸的双重夹击。溺水的人投掷石块。突然氏族会议。从沉睡的卫队的惊喜。鄙夫杀死国王。沙中推进部队的眼睛。一个双杀无血。
也有国际象棋礼仪的细微之处。保持整齐抓获的男子,往往囚犯。切勿宣布“检查”的虚荣心,以免有人用一只看不见的剑割开你的喉咙。千万不要投片到
沙箱后,你已经失去了一场比赛,因为你必须找回来,自己后,你周围道歉。夏天结束,刘蒲曾教导我,他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更好的棋手。
中国人民和游客的一个小周末人群聚集,因为我打了一个击败我的对手之一。加入我的母亲会在这些室外展览比赛的人群。她自豪地坐在板凳上,告诉我的崇拜者,用适当的中国谦卑,“是运气。”
一名男子谁看了我在公园玩的建议,我妈妈让我发挥在当地的国际象棋比赛。我的妈妈微笑着,客客气气,一个毫无意义的答案。我拼命地想去,但我咬我的舌头。我知道她不会让我上场陌生人之间。因此,当我们走回家,我说在一个小的声音,我不想在当地的比赛发挥。他们将有美国的规则。如果我输了,我想对我的家人带来的耻辱。
“耻你跌下来没有人推你,说:”我的母亲。
在我的第一场比赛,我的母亲坐在前排,因为我等待轮到我,跟我来。我经常弹我的腿,unstick从冰冷的金属座椅的折叠椅。当我的名字叫,我升腾起来。我的母亲解开的东西在她的腿上。这是她的昌举行太阳火的赤玉的小平板。“是运气,”她低声说,塞进我的衣服口袋里。我转身对我的对手,15岁的男孩从奥克兰。他看着我,他的鼻子起皱。
正如我开始玩,男孩消失,颜色跑出来的房间,我只看到我的白块和他黑色的等待对方。过去我的耳朵开始吹微风。它低声说只有我能听到的秘密。
“吹来自南方,喃喃地说。” “风留下任何线索。”我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路径,以避免陷阱。人群中沙沙作响。“嘘!嘘!”房间的角落说。风吹更强。“遥,从东沙,以分散他。”骑士上前准备牺牲。风从牙缝里,越来越响亮。“吹,吹,吹。,他无法看到的。他现在是盲目的,他瘦风远,所以他很容易击倒。”
“检查”,我说,作为风哄堂大笑。风偃旗息鼓小泡芙,我自己的呼吸。
我的母亲,放在我旁边的一个新的塑料国际象棋,邻里道社会给我的第一座奖杯。当她用软布擦拭每一件作品,她说,“下一次赢得更多,输少。”
“妈,这不是你失去了多少件,”我说。“有时候,你需要减肥片获得成功。”
“输少,看看您是否真的需要。”
在未来的比赛中,我再次取胜,但它是我的母亲,谁穿了胜利的笑容。
“失落的8件这一次,最后一次是11个,我告诉你什么?更好输少!”我很生气,但我不能说什么。
我参加更多的比赛,每一个远离家。我赢得了所有的游戏,在所有部门。从我们单位楼下的中国焙烤食品显示了我在它的窗口奖杯的成长,在一片灰尘覆盖,从未拿起蛋糕。后的第二天,我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地区赛,窗口包裹一个的新鲜搅打奶油糖霜和说红色脚本表蛋糕“恭喜你,韦弗利钟,唐人街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不久,一家花店,墓碑雕刻,和殡仪馆提供赞助我在全国比赛。这时候,我的母亲决定,我不再做的菜。温斯顿和Vincent不得不做我的家务。
“她为什么得到发挥,我们做的所有工作,抱怨:”文森特。“是美国的新规则,”我的母亲说。“美眉发挥,赢得国际象棋挤压她的大脑,你玩,值得一挤毛巾。”
我的九岁生日,我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我仍然相距约429点盛大的主人翁地位,但我是伟大的美国希望,神童和一个女孩引导吹捧。他们跑在我的生活“杂志的照片,旁边报价鲍比菲舍尔说,”永远不会有一名女子特级大师。“ “你的举动,鲍比说,”标题。
这一天,他们把我穿着整齐的塑料发夹水钻修剪修剪辫辫子的杂志图片。我是打在一个大的高的学校礼堂,痰咳嗽和新鲜打蜡的木地板之间滑动的椅子腿的吱吱作响的橡胶旋钮回荡。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名美国男子,刘蒲,也许第五十同样的年龄,。
我记得他满身是汗的额头,似乎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哭泣。他穿着一件暗,有恶臭的西装。他的口袋里塞满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头巾,他擦了擦席卷他的手与伟大的蓬勃发展选择的棋子之前,他的手掌。
在我清脆的粉红色和白色礼服,在脖子上,我的母亲已经为这些特殊的场合缝制两个沙哑花边,我想我的下巴扣下我的手,我的手肘在桌子上轻轻地准备的精致点显示方式我的母亲我冒充记者。我想我的专利皮鞋来回摆动,像一个不耐烦的孩子乘坐一辆校车。然后我会暂停,吸在我的嘴唇,如果拿不定主意捻我选择一块在半空中,然后坚决厂在新威胁的地方,它与我的对手的好办法抛出的一个胜利的微笑,。
我不再发挥韦弗利广场胡同。我从来没有去过鸽子和老部下聚集在操场。我去学校,然后直接回家,学习新的国际象棋秘密,巧妙隐蔽的优势,更多的逃生路线。
但我发现很难集中精力在家。我的母亲站在我的习惯,而我绘制我的游戏。我想她认为自己作为我的保护盟友。将她的嘴唇封紧,我每次移动后,一个软的“Hmmmmph”将摆脱她的鼻子。
“妈,我不能修炼,当你站在这样的有,”我说的一天。她退到厨房和锅碗瓢盆大声喧哗。当崩溃停止,我可以看到眼角的
余光,她站在门口。“Hmmmmph!”仅这一项就出来了,她紧张的喉咙。
我的父母做了很多让步,让我的做法。有一次我抱怨说,我共享的卧室,那么吵,我想不出。此后,我的兄弟睡在一张床上,在生活中面临街的房间。我说我不能完成我的大米,我的头没有工作的权利时,我的胃太满。我留下半成品的碗表,没有人抱怨。但是有一个工作我无法避免。我只好陪我的母亲上周六市场天,当我没有比赛的发挥。我的母亲骄傲地与我同行,参观众多的商店,购买很少。“这是我的女儿波LY钟,她说:”谁看了她的方式。
一天后,我们留下了一个店,我说下我的呼吸,“我希望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告诉大家,我是你的女儿。”我的母亲停止行走。
沉重的书包的人摩肩接踵,过去我们推在人行道上,碰到头一肩,比另一种。
“哎呀,因此与母亲的耻辱?”她抓住我的手得更紧,她怒视
着我。
我低下头。“这不是,它只是那么明显了。实在太尴尬。” “为
难你是我的女儿呢?”她的声音开裂与愤怒。“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是我说。”
“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是一个错误,说什么,但我听到我的声音说话,“你为什么要使用我炫耀吗?如果你想炫耀,那么为什么你不学下棋吗?”
我母亲的眼睛变成危险的黑色开衩。她对我无话,只是尖锐的沉默。
我觉得在我热耳风扑面而来。我猛地我母亲紧紧抓住我的手,转过身,敲成一个老妇人。她的杂货袋,洒在了地上。
“哎呀!”笨丫头!“我的母亲和女人哭了。橘子和铁罐careened 了人行道上。由于我的母亲俯身帮助老妇拿起逃脱食品,我起飞。
我在大街上赛跑,人与人之间横飞,不回头看我的母亲尖叫刺耳,“美眉!美眉!”我逃到了一个胡同,过去的黑暗,窗帘
店和商家他们的Windows洗去污垢。我加速到阳光下,到检查饰物和纪念品的游客挤满了大型街头。我躲到一个黑暗的胡同,另一条街下来,另一个胡同。我跑,直到它受到伤害,我意识到,我已经无处可去,我没有从任何运行。小巷中没有逃生路线。
我的呼吸像愤怒的烟雾出来。这是冷的。我坐了下来上翘的塑料桶旁边的空箱堆,拔罐用我的手我的下巴,勤于思考。我
想到我的母亲,向下街道第一步履轻快或其他找我,然后放弃回家,等待我的到来。两个小时后,我站了起来吱吱作响的腿,慢慢走回家。小巷很安静,我可以看到黄色的灯光,像两只老虎的眼睛在夜间从我们单位的光辉。我爬上十六步到门口,静静地推进了各不作任何警告的声音。我打开旋钮,门是锁着的。我听到了椅子上移动,快速的步骤,锁转动点击!点击!点击!,然后门开了。
“关于时间,你回家,”说文森特。“小子,你麻烦。”
他下滑到餐桌。在一个大盘子,一个大型鱼类,其肉质的头还连接到上游游泳白白逃逸的骨头仍然。站在那里等待我的惩罚,我听到我的母亲在干燥的声音说话。
“我们没有关于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没有关于我们。”没有人看着我。骨筷子碰对到饥饿的嘴巴被掏空的碗里面。
我走进我的房间,关上门,躺在我的床上。房间是黑暗的,与邻近单位的晚餐灯的阴影填补了上限。
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了一个六十四黑色和白色方格的棋盘。我对面的是我的对手,两个愤怒的黑色开衩。她穿了胜利的微笑。“不能被视为最强的风,”她说。
她的黑人男子先进整个飞机,缓缓走向作为一个单元的每个连续的水平。我的白块尖叫,因为他们急忙摔了下来板逐个。
由于她的男人靠近我的边缘,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轻。我上升到空气中飞出来的窗口。以上的胡同也越来越高,过的瓦片屋顶,我在那里聚集风推向夜空中消失了,直到我下面的一切,我独自一人的上衣。
我闭上了眼睛和思考我的下一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