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之殇之烽火霞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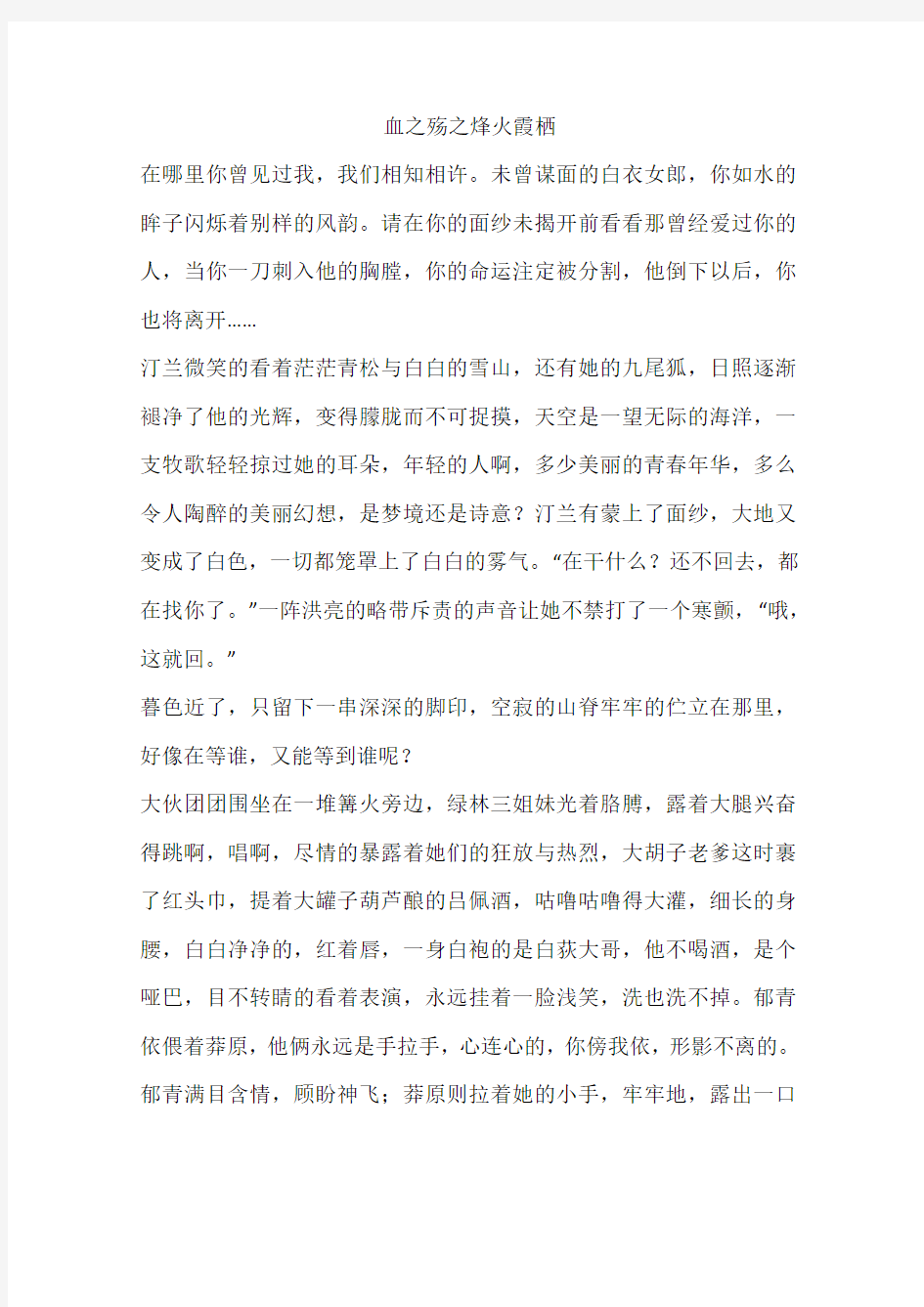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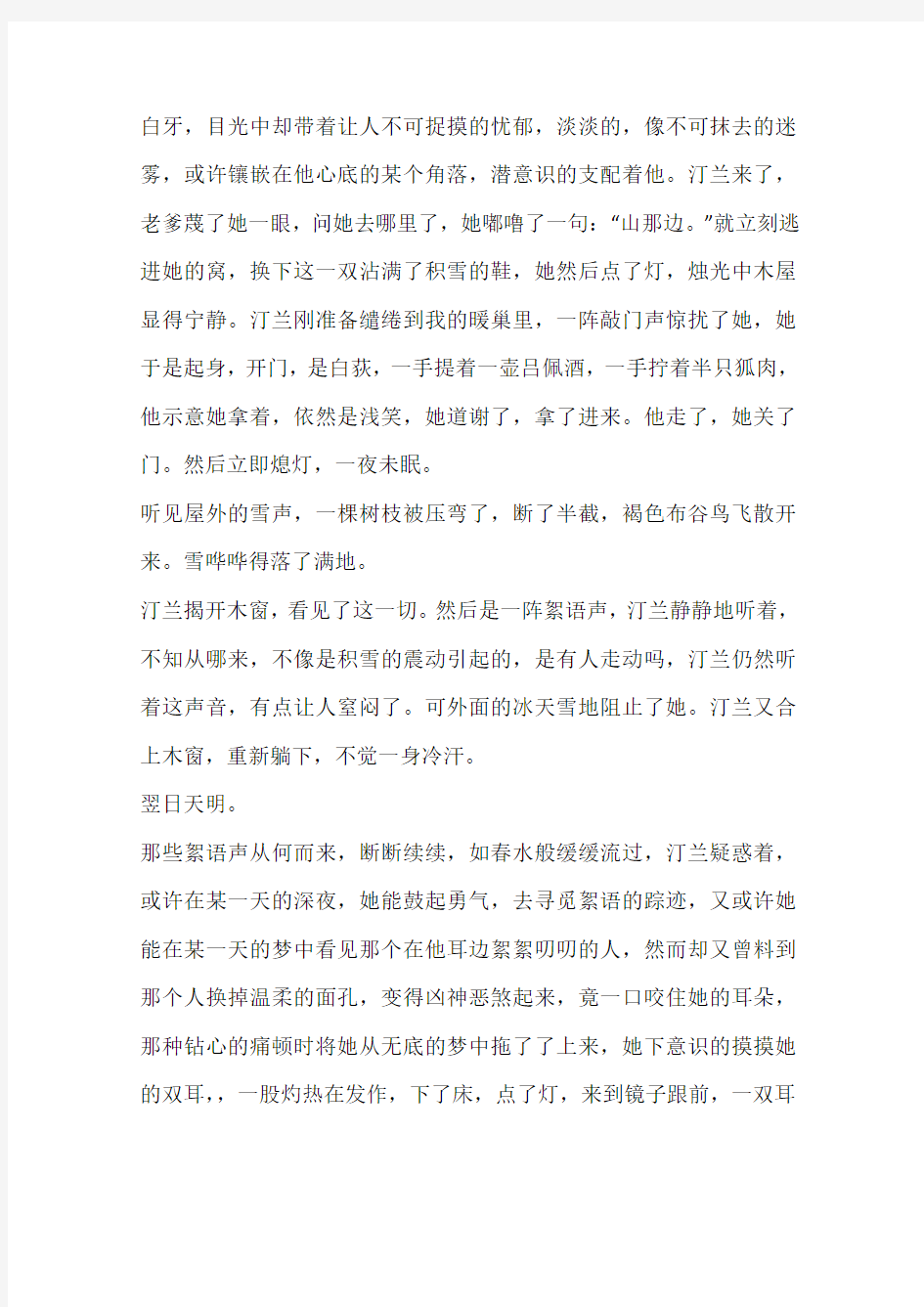
血之殇之烽火霞栖
在哪里你曾见过我,我们相知相许。未曾谋面的白衣女郎,你如水的眸子闪烁着别样的风韵。请在你的面纱未揭开前看看那曾经爱过你的人,当你一刀刺入他的胸膛,你的命运注定被分割,他倒下以后,你也将离开……
汀兰微笑的看着茫茫青松与白白的雪山,还有她的九尾狐,日照逐渐褪净了他的光辉,变得朦胧而不可捉摸,天空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一支牧歌轻轻掠过她的耳朵,年轻的人啊,多少美丽的青春年华,多么令人陶醉的美丽幻想,是梦境还是诗意?汀兰有蒙上了面纱,大地又变成了白色,一切都笼罩上了白白的雾气。“在干什么?还不回去,都在找你了。”一阵洪亮的略带斥责的声音让她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哦,这就回。”
暮色近了,只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空寂的山脊牢牢的伫立在那里,好像在等谁,又能等到谁呢?
大伙团团围坐在一堆篝火旁边,绿林三姐妹光着胳膊,露着大腿兴奋得跳啊,唱啊,尽情的暴露着她们的狂放与热烈,大胡子老爹这时裹了红头巾,提着大罐子葫芦酿的吕佩酒,咕噜咕噜得大灌,细长的身腰,白白净净的,红着唇,一身白袍的是白荻大哥,他不喝酒,是个哑巴,目不转睛的看着表演,永远挂着一脸浅笑,洗也洗不掉。郁青依偎着莽原,他俩永远是手拉手,心连心的,你傍我依,形影不离的。郁青满目含情,顾盼神飞;莽原则拉着她的小手,牢牢地,露出一口
白牙,目光中却带着让人不可捉摸的忧郁,淡淡的,像不可抹去的迷雾,或许镶嵌在他心底的某个角落,潜意识的支配着他。汀兰来了,老爹蔑了她一眼,问她去哪里了,她嘟噜了一句:“山那边。”就立刻逃进她的窝,换下这一双沾满了积雪的鞋,她然后点了灯,烛光中木屋显得宁静。汀兰刚准备缱绻到我的暖巢里,一阵敲门声惊扰了她,她于是起身,开门,是白荻,一手提着一壶吕佩酒,一手拧着半只狐肉,他示意她拿着,依然是浅笑,她道谢了,拿了进来。他走了,她关了门。然后立即熄灯,一夜未眠。
听见屋外的雪声,一棵树枝被压弯了,断了半截,褐色布谷鸟飞散开来。雪哗哗得落了满地。
汀兰揭开木窗,看见了这一切。然后是一阵絮语声,汀兰静静地听着,不知从哪来,不像是积雪的震动引起的,是有人走动吗,汀兰仍然听着这声音,有点让人窒闷了。可外面的冰天雪地阻止了她。汀兰又合上木窗,重新躺下,不觉一身冷汗。
翌日天明。
那些絮语声从何而来,断断续续,如春水般缓缓流过,汀兰疑惑着,或许在某一天的深夜,她能鼓起勇气,去寻觅絮语的踪迹,又或许她能在某一天的梦中看见那个在他耳边絮絮叨叨的人,然而却又曾料到那个人换掉温柔的面孔,变得凶神恶煞起来,竟一口咬住她的耳朵,那种钻心的痛顿时将她从无底的梦中拖了了上来,她下意识的摸摸她的双耳,,一股灼热在发作,下了床,点了灯,来到镜子跟前,一双耳
朵红肿肿地,她凑近一瞧,没有唇印,她忽然明白,那是她在梦中紧紧捂住了耳朵,因为太用力,或时间太长,才这样的。
接连的几个夜晚,汀兰的一颗心都悬着,不敢睡觉,然而一旦意识迷糊时,那个声音就嘤嘤起来,好像要对她说些什么,她竭力将恐惧抛到一边,想探询那声音的秘密,可那声音似乎从空谷传来,就像她那天驻足在霞栖山,那牧笛的旋律那般空灵而朦胧,无迹可寻,无踪可返。
天已大亮,白荻又来敲门。汀兰跟着他来到山寨,郁青,莽原,还有绿林三姐妹都来了,老爹看人都齐了,就说到:“今天有件事情跟大家商量,莽原在霞栖山的西面发现了有人出没
是一些穿这绿衣绿裤,拿着枪的人,我们必须快点撤离,看形势那些人用不了多出长时间就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做一下准备,今天下午出发。“
到了下午,血色夕阳将整个霞栖山染的一片醉意。莽原一把火烧了山寨,火苗的红和天空的红汇成一片,白雪,青松,棕色九尾狐沐浴在这红色海洋中,大地一片肃穆,人人脸上都沉积着悲情,还有一身青黛色麻纱的郁青,她的眸子里盈盈发光,“一把火就这样都烧光了吗,老爹,我真不忍心就这样烧光了…………”说着竟泪光闪闪,绿林姐妹也纷纷叹息,老爹说道:
“那些拿枪的绿贼来了,大伙就逃不了了,他家想想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是为了躲避战争,战争是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现在一无所有,
我们只有好好保全自己的性命才能不愧对我们的亲人在天的亡灵。”老爹说得身体发抖,声音也在颤抖。莽原大哥站在一边,面色凝重。汀兰和白荻忙着收拾行李。所有的一切在此时化为灰烬。太阳已落,天空泛起了一层层的鱼肚白,莽原用雪橇想把这余烬填埋掉,大家于是都干了起来,一会儿,诺大的空地就干干净净了。突然霞栖山想起了一声枪炮声,刺破了寂静。“我们该走了,”莽原大哥说道,“那些人可能就在附近了。”大家于是围成一团。老爹说:“走吧。”我们立刻下了山坡。
逃亡之旅开始了。
他们躲在了一片枯黄的茂密的草垛里,那枪炮声过后就是一片没有指望的安静了。他们意识到那些军人可能暂时不会出现,就仓皇准备下山了。莽原拉着郁青的手,白荻走在最后,汀兰则扶着老爹。
“我们绕过这条道,往西边去觅齿河,那水急湍多,水源是霞栖山的活水瀑布,据说那里水流高低深浅不一,深处如沼泽,可以吞掉人的性命,大家一定要小心”老爹嘱咐大家说;
“我们越过那条河以后会进入一片密林中那是雪山和中原的交界处。日夜天气变化无常,气温忽高忽低,我和白荻负责大家夜晚的安全。”莽原大哥发话了;
“还是我和白荻守夜吧,你就照顾郁青吧,三姐妹就照顾老爹”汀兰看着莽原的眼睛恳切地说;
郁青这时皱着眉头,竟咳嗽起来,“不用,我不用人照顾,让我跟在老
爹身边。”莽原连声问道:“怎么了,是不时伤寒复发了?要不要喝点鹿浆?”
白荻在一边看着,这会儿竟被大家遗忘了,三姐妹围在在老爹身边,寒冷的冬夜冻得她们的小脸红扑扑的,月凉如水,繁心点缀黑色的天幕,高高的雪山笼罩在暮色中,竟发出白莹莹的光,松涛阵阵,三姐妹齐声唱起了天敕歌]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姐妹阿,
生长在黑色的土壤上
美丽的松花江河,是哺育我们的爹和娘;
枪炮响,鬼子来,爹爹披上了绿军装呃,娘亲送爹爹上战场,
硝烟满天,血流成河,爹爹不知了去向呃,
一群姐妹阿,流落他乡;
我们的松花江,我们的爹和娘……三姐妹的歌声唱得哀婉绵长,凄恻动人,他们到围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听着,莽原和郁青相互偎依,他们忘着远方,似乎是绝望也是希望;白荻一只手持弄着草,紧锁着眉头,低着头;汀兰坐到了白荻身边,问他怎么了,白荻摇了摇头,汀兰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衣袖,示意他出去走走,老爹搂着三姐妹,歌声似乎越来越弱了,空山绝迹,歌声是一阵掠过的暖风。
他们来到一片布满嶙峋怪石的草地上,汀兰望着点点繁星说:“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好多好多兄弟姐妹,那时天寒地冻,外白一片白雪琉璃,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自己造了一个盆,上边放上几根削平的木
棍,然后生一堆炭火,把爹从外面打来的野兔和鹌鹄都放在上面烤,撒上酿好的吕佩酒,在兔子肚里还裹上山榉,榆钱儿,白薯干儿还有野猪的肠肚,烤出来以后就有一股浓香,姐妹几个但是不敢吃,哥哥们就大口大口的嚼起来了,我们也就放开了担子,我们是在夜晚的树龄里烤得,当时娘不见了我们,记得四处找,到了树林里看见哥哥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气得娘木栅直戳哥哥们的屁股,呵呵呵……”汀兰说着说着竟哭了出来,“后来哥哥们当兵的当兵,做汉奸走狗的也有,咋就弄的互相残杀,你死我活了。”
白荻静静地听着,然后用口含石子般的声音说道:“别哭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汀兰兰治住了眼泪,略带羞涩略带惊恐地看着白荻,白荻正痴痴地望着自己,汀兰赶忙收回眼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的瓶子,掺杂着各种难以言状的情愫,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她心里装着谁。白荻似乎很艰难的想说什么,可因为他身体的缺陷,他的话说出来时,音调扭转成各种音符,一顿一顿,没有连贯的话,只有一字一字的口型。但是汀兰他们习惯了,他们不仅习惯了白荻说话的方式,也习惯了他古怪的举止与神情,他虽然有一脸不落的灿烂,但是别人都不爱搭理他,他品时都不住在山寨,白天老爹和莽原去山上打猎,白荻也跟着去,回来的时候老爹和莽原打回了山鸡和野兔,白荻却没有回来,只有到夜里摸黑时分,他才兴冲冲拧会几条长蛇,活生生的吐着芯子,觉得白荻着孩子精神有点不正常,行踪诡异,不可捉摸,而且看起来不伦
不类,活像个女孩子。大家都不爱搭理他,就任他一人做自己的事情。汀兰也知道,或许是出于怜悯,汀兰也就没有拒绝他,但是汀兰心里也有主张,她可以把他单做自己的亲弟弟,仅此而已。
月色清冷,寒鸦栖枝,星辰点点。汀兰好像困了,就靠在白荻的肩上睡着了。
夜里,一阵絮语似乎从很遥远的山谷传来,断断续续,若影若现。汀兰只觉得耳朵开始一阵敏感,然后钻心的痛扑袭而来,犹如无数个梦中,有人在撕扯他的耳朵,她吓得满身冷汗,恍恍惚惚的,她捂住了耳朵,挣扎着,“不要咬我,不要,不要……”突然一声凄厉的喊叫把她从梦里的悬崖救了回来,她突然睁开了眼,发现自己躺在一条木舟中,正随着激流逆水而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白荻呢,白荻呢……”夜色更沉了,汀兰看着这急遽的河流只要把她带到哪里,就吓得哭了。木舟突然碰到了水中的一块石头上,停了下来。汀兰敢忙起身,想跳在那块只有她双脚那么大的石块上,于是她伸出了左脚,向前一跃,脚掌一阵疼,突然石头开始下沉,汀兰“哇”的一声又飞一般跨入船中,石头迅速没入水中,一点声响也没有,汀兰脑子了突然闪现了莽原的话:“觅齿河水急湍多,深浅不一,深处如沼泽,可直吞人性命。”想到这时,汀兰方觉天昏地暗,如果从船上跳下来她恐怕会葬身河底,可这船又不知驶向哪里。现在已经和老爹他们失去了联系,她该怎么办呢?
老爹他们呢,此时正分头找着汀兰,汀兰不见了,白荻也不见了踪影,
可他们知道白荻平时就神出鬼没的,可汀兰呢,她怎么也就失踪了呢?莽原若有所思,他没有去找。郁青刚从山坡下回来,说:“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们俩。”老爹于是镇了镇神,说道:“天快亮了,我们边走边找,在沿途中留些标记,如果他们找不到,或许会看见我们留下的记号,追上我们。”绿林姐妹中的小眉说:“汀兰姐姐在我们大家动身之前,曾经去过霞栖山,回来就变得很古怪了,夜里经常说梦话,我和他的房之隔一扇门,听得清清楚楚。”莽原这时低下了头,他似乎声么花都不想说,目光中流露出少有的冷峻,郁青说:“汀兰到哪里去了呢?我么还要一起寻觅一处世外桃源,过姐妹相亲的日子了……”说着又泪光楚楚,莽原握住了他的手,说:“没事,一定可以找到的。”
汀兰此时正身陷木船,不知所措。黎明的曙光降临了,透着这微光,汀兰看见了荒蛮一片的枯原。无数的泥潭,阴森的树木,还有远处一堆堆坍塌的废墟。不知是么东西呱呱的怪叫,一声接着一声,她的心一点一点地沉落了,她感觉到窒息,这条河竟然泛着褐色的斑点,她伸出手想摸摸这是什么东西,可手刚一碰,鲜血就汩汩直流,她吓住了,不知知是什么鬼地方,不知怎么来这里,更不知以后会怎样,想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嘤嘤地哭了起来。船飘摇着,不知不觉停了下来,她抬起头,只见一具尸体正浮在河上,他的脸色发青,嘴唇乌紫,颧骨高高的凸起,上身赤裸着,穿一条绿军裤。她愣住了,立刻拉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拽到船上来,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他拖上来了,他的肚子鼓胀胀的好像溺水了,于是她按住他的肚
子用力向下摁了几下,满口褐色的水就流了出来,那人猛抽一口气,大声咳嗽起来,“你醒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汀兰好奇地问道,“你呢?”那人望着面前这个眉清目秀,粉面含春的姑娘,也问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这里了”汀兰不解的说,那人点了点头,似乎知道了什么,有说到:“你知道你来哪里了吗?”汀兰摇了摇头,那军官叹了口气,“我们是在狼人山庄,这里游走着很多狼人,他们会剥人皮,喝人血,尤其爱吃少女,你可能是被他们抓到这里的”汀兰听的惊慌失色,“可他们……为什么没有吃我呢?我又怎么会在船上?”军官若有所思,又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个问题。”“那你呢,你怎么会溺水的?”“我是红军,被部队派来勘查这里的地形,昨天晚上随同几个兄弟潜入这里,碰见了野人充溢着她的心,”你怎么了?“那军官看见汀兰低垂着脸,郁郁寡欢的样子就问道,汀兰回答:”没什么,我不喜欢军人。“军官深深的叹了口气,说:”我讨厌战争,但是不讨厌军人,战争摧毁了我们的家园,害死了我们的亲人,军人被迫拿起武器来抵御外侵,保护我们的国家,用流血牺牲来换取自由和独立。“汀兰听了恍然大悟,把她的几个哥哥送上站场的不是军人,而是战争,不是这些穿绿衣绿裤,佩戴红星勋章的军人,而是那些发动战争,炸毁她家园的鬼子们。想着想着,他不禁握住拳头,咬牙切齿起来。军官看到面前的这位弱不经风的姑娘竟流露出如此神情,哈哈大笑。汀兰见他笑了,又不好意思起来,嗔怪道:”大哥,你笑什么啊?“愈发觉得这姑娘可爱至极,就不禁伸手要为她擦
拭脸上的丝丝泪痕,汀兰忽一抬头,正碰上军官的手,又瞥见他壮实的胸膛,不禁一阵面红耳赤,轻轻推了一下军官的手,军官怔住了,呆呆的望着汀兰。汀兰心里也扑通的直跳,扭过头,眺望远方。汀兰问军官:”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周霁雨,你呢?“军官回答。”汀兰。“
半晌无语。
而此时的莽原和郁青他们正快速向前,因为他们已经暴露了行踪。这还得从今早说起,莽原带着郁青沿路走时,忽听见前方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就潜伏在了一片密密的荒草中,只听见不远处有人好像在说:“这一带一定有人出没,一定不能放走那些红军,还得利用他们对付那些狼人,不然没法度过觅齿河了”,“嘿,一定照办,那些红军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莽原他们屏住呼吸,静静听着,原来这些人竟是一些汉奸走狗,假扮成红军的装束,其实是为了当奸细,探听内情。看着那班人走远了,他们便出来了,继续赶路。老爹却停住了脚步,对大伙说:“我们已经在这些绿衣贼的包围中了,恐把迟早是要被发现的。我们最好分成两路,这样可以加速行程,大家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就大,你说呢,莽原?莽原点了点头,说:”我和郁青往南边走,老爹带着三姐妹王北边走,霞栖山是一个回环的地形,我们出山以后,就是方圆十里的弱水镇,到那时我们再相会。“莽原有看看郁青,郁青点了点头,三姐妹也点头说好,老爹最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没有其他办法了,为了躲避战争,我们有缘聚在一起,现在外人破坏了我们平静的
生活,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老爹心里明白,你们都还是年轻气盛的孩子,都还恋者外面的花花世界,老爹委屈你们的心愿了。“郁青听了,眼泪又吧嗒吧嗒的往下掉,紧紧握住老爹的手,说:”老爹,若不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平静的世界来,我们早已被外面的炮弹炸成白骨了,老爹,我们出山后一定马上找到您,我们就有在一起了“老爹听了,鼻子一酸,抹起了眼泪,三姐妹连声劝到:”爷爷,别哭……“待莽原嘱咐了三姐妹几句,两路人就此分开了。此时的郁青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她想象他们还会再弱水镇相聚,那时汀兰和白荻都回来了,他们能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她还能像在霞栖山那样每日沐浴朝阳与晚霞,跟着莽原哥哥上山打鹿,夜晚为在篝火边和三姐妹唱歌跳舞,而她怎么也没想到等待她的会是永别,她再也不能看见她的老爹了,再也不能看到她的伙伴们了,这一别,或许是天堂的结束,也是地狱的开始。这个璞玉浑金般的天使,会深陷泥淖,而推她下水的,则是一个她死后都不会相信是他干的的人。
莽原和郁青走得很快,待到日落时分,他们在一片芦苇丛中坐下。莽原对郁青说:“饿了吧”郁青摇了摇头,莽原揭开形囊,拿出吕佩酒和一些干粮,然后把干粮掰碎,俯下身去,一点一点地喂给郁青,就像喂给一只自己心爱的小白兔,那么专注,那么柔和。莽原自己则咕噜咕噜的喝起了酒,他就像一个飞驰在塞北高原的大侠,停下匆匆的行走,对酒高歌,身旁还偎依着他的红颜知己。莽原突然把郁青搂在了怀里,不,应该是搂在了胸口,紧锁双眉,哽咽得喃喃自语道:“对不起,对
不起,对不起……”莽原第一次这么激情的拥抱让郁青心中不禁一阵颤栗,她静静的靠着,她深爱着他。太阳放慢了脚步,地面的影长不再移动,时间停住了,仿佛那一刻就是永恒。
等他们睁开眼,声旁却围了一大班绿衣军人,郁青吓得罗嗦起来,莽原抱住了她,“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只见那几个军人拿出几根粗绳,把他们俩拆散开来,然后绑住。那个似乎是带队的秃头先看了看莽原,目光中掺杂着几丝冷笑,怪声怪气地说:“小子,你还真让我们
好找啊,“然后立刻调转目光移向了郁青,满脸的怪气变成了一股媚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似乎还冒着金星,看得郁青毛骨悚然,”真是绝世美人啊,简直不食人间烟火,那人呵呵地狞笑着,是个纯货……“郁青再也听不下去了,捂住了耳朵,莽原厉声喝到:”不许你们碰她!那人又转向莽原,哦,还是一对啊,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棒打鸳鸯的滋味!“说命令手下把他们带走。郁青此时仿佛天旋地转,脸上的泪痕是流淌的小溪,谁怜岸边幽草,总把一腔愁情付之东流水。莽原低垂着头,这个曾经爬过雪山,喝过鹿血的汉子,从未在任何风霜雨雪前低过他高贵的头,可现在,在这些枪支弹药面前,他却低下了头,郁青看在眼里,泪珠更是决了堤的洪流。他们被带到山中的一处隐蔽的洞穴中,那几个士兵打着几把火,把整个洞穴照得通亮,两边的石壁上都挂满了水,洞穴里冷得出奇,他们沿着那狭窄的缝隙向前走着,忽让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都带来了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嘴角还留了一撇小胡子的人,郁青立刻明白了,他不是中国人。”本幕
上校,我们已经跟踪他们好几天了,却不料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好在小的悟性高,在一片芦苇地里发现了这两个,另外的都逃跑了。“只见那人直盯着先前的这位出水芙蓉,目光中流露的则是诡异的暧昧,没有回应他的话。然后转过头对那秃头说:”你把她带到最里面的洞里,好好伺候,我可不想看到她的一张哭丧脸,要不然,小心你们的脑袋。“郁青被他们带走了,只留下了莽原。郁青坐在那个冰冷的洞窑里,刺骨的寒冷让她忘记了所有的痛。不知道莽原在那里做什么呢,莽原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呢?她在心中默念着莽原的名字,希望今晚过后明天醒来一切都是一场梦。可这不是梦,而且现实也不会理会一个无关的弱女子悲恸的嚎叫,不该发生事还是发生了,该来的人不会再来。郁青蜷缩在山洞的一角,睡意侵袭,她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下意识好像有人在握她的手,她第一反应不是本能的清醒,接着是她的头发,她的脸甚至她的耳朵,她觉得有一股热流迅速灌注全身,她对这股热流的依赖超过了她睁开眼的理智,可突然意识自己胸口一阵冰凉,她打了个罗嗦,猛地一下睁开了眼睛,那个被称作本幕的小胡子正在吻她的胸口,她啊的一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推开他,然后捂住胸口,莽原,快来救我!然后立刻朝出口处奔去,笨重冰冷的石门把她堵住了,她回头望了望一脸阴气得本幕,疯狂的扑了上去,咬住本幕的手臂,”你这个禽兽……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本幕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摁在地上,郁青的口里混杂着血泪,仍然哭喊着,一声一声叫着莽原的名字,本幕冷笑道:”你的莽原已经成了我的得力助手,他向我透露了
你所有的秘密,嘿嘿,小娘么,你可是我费尽心思弄到的尤物,乖乖听话,忘掉你的莽原,只记住我本幕一个,否则,你的莽原也救不了你了。“说完轻轻在她脸上捏了一下,”宝贝,好好休息,我走了“说完整了一下他的衣服,打开石门走了。郁青只觉浑身无力,一下子瘫在了地上,目光呆滞,望着空空的石壁,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了,或许说是她再也不愿想什么了。
无泪,无语,无情,无心。
郁青就在那里坐了三天三夜,眼望着石壁,目光呆滞,没有表情。
不管谁去看她,她只说一句话:“我要见莽原。”
本幕来了,依旧是一脸的阴沉。他走到跟前把瘫软的郁青搂起来,抬住他的下巴说:“你知道你日思夜想的莽原是什么样的人吗?哼哼,他可比我厉害多了,你知道那天怎么会在芦苇地被我们逮住的吗,是你的莽原通知我们,让我们埋伏好,等着你们上钩。他现在快和我平起平坐了,被皇军升为副上校,正春风得意了,他把你献给我,其实也是为你好,如果献给我们的皇军司令,恐怕您的冰雪之身,早就给毁掉了厄……”说完又是一阵阴森的冷笑。
让人听得毛骨悚然。郁青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疯了一般的抓住本幕得衣服,摇摆着,“不可能,你骗我,不可能……”说着说着,就晕了过去。这一晕,郁青的生命也像冬天枯木上即将凋落的叶子,摇摇欲坠。
那天,天气很好。她躺在本幕为她特意装备的木床上,厚厚的几层狐皮裹在她的身上,她仍然觉得很冷很冷。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让她圆睁
着眼,仔细听着。其实,她对每一种脚步声都特别敏感。有人进来了,他穿着黑色的皮毛大衣,戴着别有徽章的军帽。她的眼睛中有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也有一种她很陌生的东西,那个人蹲了下来,只是看着她,没有碰她,也没有说话。她的嗓子已经嘶哑了,但她还是想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她想要说的话。“莽原,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去过的原青林吗,就在霞栖山上,很小很小的一片白桦树林,我死了,你一定牙把我带到那片树林里,把我的身体埋葬在树下……”说完,郁青闭上了眼睛了。她的脸白得就像一张透明的纸。莽原站了起来,遥望着远方那座它们共同拥有过的霞栖山,一滴泪滚落下来。
他派了几个手下把郁青的尸体护送回了霞栖山,原青林,那片白桦树下,埋葬好。也许那就是郁青的家吧,这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细雨般温婉,杨柳般纤弱的女子,这个在炮火中被莽原救出来的女子,在他的爱人背叛他后,安然地睡着了。躺在沧桑的白桦林中,枕着他和他的爱人曾经留下足迹的土地上。她安然入睡,她依然很美,透着几分淡淡的忧郁,犹如清涧边幽幽的青草,迎着风,向着阳,默默守候着一生的爱情。
汀兰和周霁雨在一起,他们早已摆脱了觅齿河的束缚,来到了狼人山庄。
本幕在听取了莽原的建议后,决定带领他的部队往觅齿河方向前进,他们要在狼人山庄布下天罗地网,活捉那帮狼人,并且一举歼灭与他们相持了数周的那帮红军。
狼人山庄总在深夜三更时四周响起凄厉悱恻,悚人入骨的长啸声。就在那天夜里,汀兰似乎觉得这声音就是他梦里的真实,和他梦境中听见的感觉一样。她心里疑惑着,没有跟周霁雨说。一只硕大无比的黑爪突然从身后突袭而来,她头一晕,周霁雨立刻放枪,她回过头,高出她一截的一只黑乎乎的怪物,正面目狰狞的望着她,那只怪物有着狼一般锐利突兀的牙齿,一双眼睛凶光炯炯,他的身躯就像远古的猿人,只见那狼人就要向汀兰扑来,周霁雨上前一拦,一拳打在了狼人的头上,浪人的腹部已经中了一枪,鲜血顺着黑色的毛向下流。狼人捂
住了伤口,双掌击中了周霁雨的头部,周霁雨倒下了,汀兰啊的一声,整个身体悬浮在了空中,她被狼人夹在腋窝下,浪人飞奔走了,周霁雨忍着剧痛,紧追其后。不一会儿就甩开了周霁雨,消失在黑茫茫的灌木林里。汀兰死命挣扎着,突然听见一阵口哨声,仿佛命令一样。狼人停下了,一个披头散发,光着身体,下躯裹着一张花斑蛇皮的怪物出现了,待汀兰仔细一瞧,不是别人,而正是那天晚上和他失散了的白荻!白荻开始没有管汀兰,他观察着狼人的腹上的伤口,然后掏出一只匕首模样的利器,刮开它的腹部,然后掏出那颗子弹,狼人平躺在地上,发着颤抖的呻吟,听得汀兰毛骨悚然。接着,白荻转过头看了一下汀兰,用他在
霞栖山独有的“语言”,对汀兰说:“我要借你的血”,汀兰吓得不敢吱声。白荻用他的刮腹刀,朝向汀兰,然后把汀兰按在狼人的头部,汀兰的
整张脸都被狼人吞了下去,汀兰感觉她的脸刺入了齿轮,钢刀,千万颗竖立的刺上。汀兰知道,她的整张脸全毁了。狼人的呻吟止住了,汀兰似乎觉得自己和他们也是同类,白荻松开了手,汀兰没有捂住自己的脸,她冷冷的看着白荻,冷冷的笑了起来。满脸的血污,杂乱的伤痕,一轮一轮的齿印,白荻却显得很平静,他注视着汀兰,他说:“这样,你就永远可以留在我身边了。”汀兰哇的一下大哭起来,撕心裂肺地喊道:“为什么?…………”她朝觅齿河的方向飞奔过去,白荻一把抱住了她,汀兰挣扎着,白荻抱得更紧了,说:“我们都是怪物了,我再也不会担心有人会爱上你了……”汀兰抓住他的脸,像抓住一条蛇,死命地拧着,说:“你这个疯子,我不会留在这里的,放我走,放我走,我要走……”哭着哭着就哭晕过去了。觅齿河冷冷的流着,它流淌着褐色的血液。
周霁雨顺着狼人的脚印,终于踏进了狼窝。不料竟中了埋伏。一群狼人围住了他,他掏出枪,刚想开,就被背后的一个狼人抢去了,他被那群狼人绑住了,白荻出来了,赤裸的上身,蛇皮围着的下身,一脸洗也洗不掉的笑。“你是不是把一个小姑娘也抓到这里来了?”白荻没有回答,他不想暴露他的语言。汀兰醒了,听见外面一片喧闹,她被绑在黑黑的木屋里。
枪炮声起,白荻顿时紧张起来,他又吹起了他象征命令的口哨,然后骑在一个高大的狼人身上,风一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白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是汀兰。周霁雨却早已跑到那间小木屋里了,看见眼前的
汀兰满脸血污,口中喃喃自语的不知说什么,周霁雨立刻抱住了她,替她松绑,抱着她冲出了小屋。一颗炸弹落在了狼人山庄,紧接着就是军队的整齐步伐,周霁雨知道日本鬼子已经来了,这回恐怕凶多极少。但是他很镇定。莽原带着一路兵在整个狼人山庄搜寻着,脚步逐渐临近,周霁雨自动献身了,他扶着身边的汀兰。莽原先是一怔,让后又恢复了以往的冷峻。汀兰不敢睁眼,周霁雨对汀兰说:“你哥哥来了。”汀兰慢慢睁开了眼,“是莽原大哥,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郁青呢?”莽原被问得脸色苍白,他看了看周霁雨,冷冷的说:“你怎么知道我?”“你叫莽原,曾经和几个同样为躲避战乱的人隐藏在霞栖山,包括汀兰。后来我们发现了这里,你们不得不分散,你为了保全自己,拿你的妻子做交易,你成功的坐上了副上校的交椅,为日本特种兵效力,所谓特种兵,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说的奸细。”周霁雨一字不差的说了出来,汀兰狠狠地盯住莽原,说道:“老爹和郁青呢,他们到哪里去?”周霁雨又说:“他们已经死了。”汀兰禁不住捂住了脸,莽原顿时面露凶光,说:“你应该就是红军第45路兵团侦查队的队长周霁雨,呵呵,真是狭路相逢啊,你现在已经身陷我们的包围圈中了。”“没错,你们现在就可以逮捕我,可我告诉你,霞栖山外还有个弱水镇,我的弟兄们已经在那里等候你们多时了,你们一出霞栖山,就是自投罗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周霁雨,你以为这就可以骗我吗,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也别忘了,这是狼人山庄,狼人是不嗜人性的。我们可以互利共生,你懂吗?”周霁雨依然泰然自若,莽原讥讽
道:“你也不过如此,呵呵,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汀兰松开周霁雨的手,说:“周大哥,你怎么能和这种人合作?”周霁雨看了看汀兰,目光坚定,说:“跟着我走吧。”
乌云遮住了太阳,天空彤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狼人山庄笼罩在一片青色的雾霭中,,雷鸣滚滚而来。狼人哀啸,遍地生棘。周霁雨对莽原说:“狼人只有在夜间才出来觅食,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那片黑树林里,它们习惯运用啸声来离散人的意识,人若在睡梦或在幻觉中能感觉它们的啸声,可能就成为了它们摄中的对象,它们剥人皮,喝人血。我们如果能模仿它们的语言,或许就能防止意识的离散,然后掌控它们。”莽原说:“怎么模仿?我们是人,不是狼。”“你的同伴中有个人,叫白荻,他已经同化为狼人了。”周霁雨说道,然后握住汀兰的手,“汀兰,你懂我的意思,对吗?”汀兰望了望身边这个人,点了点头。周霁雨对汀兰说:“天亮的时候,周大哥会在觅齿河等你。”
汀兰独自一人走进了黑森林。她边走边喊着:“白荻……白荻……”白荻站在汀兰的背后,汀兰一转身,恰好碰到了他。白荻的样子很吓人,不过与之前的不同。汀兰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她用一条丝巾蒙住了脸。白荻说:“你怎么来这里了?”“那些军人将整个山庄搜遍了,没见到一个人,就撤离了。她们见我没用,就把我放了。”汀兰说得很轻松。白荻接着问:“那个来救你的军人是谁?”“他们是一伙的,跟着军队走了。”白荻走了,汀兰跟在身后。白荻比汀兰还小,在汀兰眼中,白荻始终是个孩子,她知道白荻过于痴情才会毁掉她的容貌。汀兰和他来到了
他住的小木屋。黑洞洞的木屋里只有一只大得出奇的水缸,汀兰走上一瞧,竟盘曲这无数细长的白蛇。汀兰佯装镇静。然后对白荻说:“白荻,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了。”白荻突然问道:“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汀兰上前主动握住白荻的手说:“我们以后相依为命,好吗?”白荻愣住了,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他把汀兰抱在怀里说:“兰,我等着天都等了多久,你知道吗?你还记得晚上我们在霞栖山上,一起看月色,你说了好多话。”汀兰觉得那件事肯定和白荻有关,就问道:“那天我睡着后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条木船上,你不见了。”白荻说:“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狼人山庄这个地方了,我和这里的狼人成了朋友,慢慢的我明白了它们之间也是互通语言的。我逐渐学会了它们的语言,它们内部就像我们人类,只有在面对陌生的人时才会流露出狼的本性。”汀兰觉得他在逃避问题,就说:“你一定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对吧?”白荻说:“我想把你据为己有,我不想看到莽原,他在暗地里使坏,陷害我,在老爹面前总占据我的功劳,因为我当时斗不过他,就像带着你走。你不爱我,我没办法出此下策。”“那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船上呢?”“顺着那条河到尽头,就是狼人山庄。我在那等着你,可是事情没如期进展,你被人救走了,就是那个军人。”“然后你就为了报复我,就把我推入狼口,是吗?”“不是!我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一切已经真相大白。汀兰觉得这世间一切都是那么让人难以预测,
所有人都敬爱的莽原大哥,他们的莽原,竟是卑劣狠毒到如此地步!
